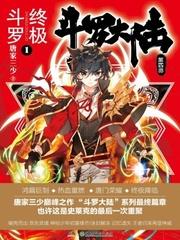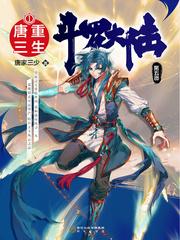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堪破三千世相

堪破三千世相
本书中的所有内容均属杜撰,不代表真实情况。本书是对人情世故的本质解析,揭示人际关系中更隐蔽的博弈维度。夫鸿蒙初辟,人伦肇始。往来成古今,交游化经纬。今有世道幽微处,潜龙隐鳞,白虎藏爪,非明镜无以照形,非灵枢何以度势。故作此篇,解构人间棋枰,勘破三千世相。是书凡六十卷,暗合甲子轮回之数。论市廛之交、庙堂之谋。析情伪之 堪破三千世相
《堪破三千世相》第3章 红楼朱门锁灵玉
笔墨纸砚,一把攥住胭脂钗环。贾政拂袖而去的声音惊飞檐下春燕,那句"将来酒色之徒耳"的判词,从此如金锁般坠在这位怡红公子颈间。十年后大观园试才题对额,他脱口而出的"沁芳"二字本已满座惊艳,偏被父亲冷笑:"不过些精致的淘气!"那卷《姽婳词》在指尖捏出褶皱,墨迹洇开处恰似少年心头化不开的块垒。 金簪雪里埋 宝玉的困境,恰似被锁在赤霞宫神瑛侍者的那缕精魂。封建世家的"抓周"仪式,本质是《周易》"观物取象"的异化——将婴儿的本能动作解读为命运谶语,正如相士用《麻衣相法》框定人生轨迹。这种标签化的宿命论,在曹雪芹笔下化作"正邪两赋"的判词:通灵宝玉本是补天遗材,却被世人看作沉湎闺阁的顽石。 这种认知暴力,实则是礼教秩序的延伸。《礼记》中"男子生而弄璋,女子弄瓦"...
《堪破三千世相》最新章节
- 第3章 红楼朱门锁灵玉
- 第2章 卧龙岗上待时飞
- 第1章 寒梅岂肯屈枯枝
- 第15章 青山依旧在超越人设的终极智慧
- 第14章 残荷听雨声崩塌废墟中的精神重建
- 第13章 断尾求生术主动崩塌的避险艺术
- 第12章 破茧未必成蝶崩塌后的重生之道
- 第11章 蜃楼海市幻复空数字时代的集体崩塌症
- 第10章 枯木借春终萎谢虚假人设的供养危机
- 第9章 沐猴而冠终露尾身份僭越者的现形记
- 第8章 彩云易散琉璃脆完美主义的崩塌前兆
- 第7章 画地为牢终自困人设构筑的认知陷阱
《堪破三千世相》章节列表
- 前言 世情赋
- 第1章 寒梅立雪见真章困境帮扶的本质奥秘
- 第2章 四公子养士之道战国门客制度的投资密码
- 第3章 漂母一饭定乾坤从韩信故事看预期价值
- 第4章 红拂夜奔识英雄风尘中的精准识人术
- 第5章 吕不韦奇货计高风险人情投资博弈论
- 第6章 宋江及时雨之谜水浒传中的雪碳经济学
- 第7章 范蠡三散千金术雪中送炭的止损智慧
- 第8章 管鲍之交生死鉴千古知己的投资法则
- 第9章 红顶商人胡雪岩晚清银票里的雪炭经
- 第10章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错付真心的千年警训
- 第11章 诸葛出山三分计隆中对里的战略投资
- 第12章 季札挂剑践心诺春秋信义的雪炭哲学
- 第13章 沈万三聚宝盆传说明代巨富的雪炭陷阱
- 第14章 柳毅传书救龙女唐代传奇中的机缘转化
- 第15章 雪炭智慧现代鉴古法今用的处世法则
- 第1章 金缕玉衣下的捧杀陷阱
- 第2章 洛阳纸贵背后的利益暗流
- 第3章 曲江宴上的彩云易散
- 第4章 牡丹亭外锦灰堆
- 第5章 铜雀春深锁二乔
- 第6章 大观园里的螃蟹宴
- 第7章 滕王阁序的蝴蝶效应
- 第8章 甘露之变中的甜味砒霜
- 第9章 东坡肉里的世态炎凉
- 第10章 沉香亭北倚栏杆
- 第11章 洛阳珈蓝记中的浮世绘
- 第12章 兰亭集序的墨色江湖
- 第13章 长门赋金换不回恩宠
- 第14章 霓裳羽衣曲中的权力舞步
- 第15章 桃花扇底送南朝
- 第1章 和氏璧与十五城
- 第2章 管鲍之交的青铜秤杆
- 第3章 范蠡三迁的智慧
- 第4章 丝绸之路的查码密码
- 第5章 红楼梦里的螃蟹宴
- 第6章 水浒传的投名状
- 第7章 徽商典当行的木算盘
- 第8章 科举考场外的幕帘
- 第9章 清明上河图的桥头市
- 第10章 庄子寓言中的屠龙术
- 第11章 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
- 第12章 徐霞客游记的驿路账本
- 第13章 盐铁争论的幕后博弈
- 第14章 聊斋志异的狐仙契约
- 第15章 园冶古籍中的假山石
- 第1章 从大观园看等级基因
- 第2章 弼马温的职场启示录
- 第3章 九品中正制的千年回响
- 第4章 李逵的悲剧突围
- 第5章 和珅的登云梯
- 第6章 林黛玉的教养课
- 第7章 诸葛亮的三拜之礼
- 第8章 白居易的折中之道
- 第9章 包公的三把铡刀
- 第10章 贾谊的早逝之谜
- 第11章 杜十娘的百宝箱
- 第12章 范进的癫狂时刻
- 第13章 柳湘莲的游走智慧
- 第14章 探春的改革困局
- 第15章 陶渊明的突围样本
- 第1章 宰相门前七品官
- 第2章 读心术
- 第3章 情绪价值的艺术
- 第4章 实力输送的隐形通道
- 第5章 危机中的进阶之道
- 第6章 信息操控术
- 第7章 平衡的艺术
- 第8章 反制之道
- 第9章 语言陷阱
- 第10章 角色扮演
- 第11章 风险对冲
- 第12章 利益共同体
- 第13章 进退时机
- 第14章 人格面具
- 第15章 终极法则
- 第1章 三国鼎立中的制衡密码
- 第2章 合纵连横的蝴蝶效应
- 第3章 大观园里的微缩江湖
- 第4章 盛唐藩镇的天平游戏
- 第5章 水泊梁山的权力暗流
- 第6章 西游取经团队的制约艺术
- 第7章 内阁首辅的走钢丝哲学
- 第8章 清河县的灰色天平
- 第9章 督府制度的双刃剑
- 第10章 阴阳簿上的生死秤
- 第11章 质子外交的蝴蝶骨
- 第12章 科举场外的隐形天平
- 第13章 游侠江湖的规矩方圆
- 第14章 市井茶楼的平衡哲学
- 第15章 千年平衡术的现代启示
- 第1章 道德利剑初铸
- 第2章 法理与道德的千年拉锯
- 第3章 血清枷锁的沉重
- 第4章 忠义旗号下的暗流
- 第5章 江湖义气的双面刃
- 第6章 家族责任的温柔牢笼
- 第7章 孝道绑架的千年困局
- 第8章 清官人设的致命陷阱
- 第9章 家国大义的暗面